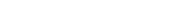随着私募基金行业的快速发展,一些潜在的结构性风险也逐步暴露,尤其在基金管理人“失控”、项目公司实际控制人规避责任,或董监高“失联”等极端情形下,投资机构往往陷入治理瘫痪与维权困局。近年“爆雷”案例中,管理人怠于履职、失联逃避责任的情形不断上升,这不仅动摇了基金治理的根基,也暴露出基金制度设计和风险应对机制的薄弱。
在这种“治理真空”下,如何合法接管基金事务、有效主张权利、维护资产安全与LP合法权益,成为私募机构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本文将从私募基金组织结构、法律赋权路径、实践难点与应对机制四个方面展开分析,系统探讨私募基金机构在面对管理人失控或董监高失联时,如何构建应对方案,实现风险可控与资产保全的双重目标。
一、管理人“失控”的真相
在私募基金运作过程中,“管理人失控”与“董监高失联”是引发基金运转中断、投资人权利受损的两类典型风险情境。具体而言,“管理人失控”通常包括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基金管理人因涉嫌违法违规被监管机构调查、控制人或核心人员被刑事拘留;
·管理人擅自变更基金重大事项或资产处置方案,严重背离基金合同约定;
·管理人拒绝或无力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停止对投资人查询、会议召集等事项的响应;
·管理人在关键节点失联,导致基金重大事务无法推进。
相较之下,董监高“失联”风险则多出现在项目公司(即基金投资标的企业)层面,其具体表现包括:
·企业董事、高管长期无法联系,导致公司无法召开董事会或形成有效治理意见;
·公司治理体系名存实亡,重要经营事项长期处于“无人决策”状态;
·项目公司资产失控、账册资料缺失或财务审计受阻,严重影响基金投后管理与退出安排。
造成上述风险的根源往往在于基金设立初期治理结构设计失衡。例如,GP集中掌控运营权但缺乏制衡机制,LP对基金运作缺乏实质参与,投资项目公司缺乏强有力的财务与信息监管手段。这些隐患在基金早期可能未暴露,但在管理人或董监高发生变故后则会迅速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二、失控之下,谁来出手?
面对基金管理人“失控”或项目公司董监高“失联”所带来的治理障碍,私募基金机构须迅速评估现有合同机制与法律工具的适用空间,果断采取合规且有效的权利主张路径,以防风险持续扩大。根据不同风险情形,私募机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启动投资人会议机制,推动重大事项决议
多数基金合同或章程设有“投资人会议”条款,用于在管理人失职或争议事件中由LP集体作出决策。机构可依照合同约定召集投资人会议,并提请表决以下事项:
·更换基金管理人或指定临时管理人;
·授权专业机构接管基金账务、推进资产追偿;
·发动诉讼或采取资产保全措施。
若合同中对召集机制未作明确规定,亦可参考《合伙企业法》相关规定,依据“过半数合伙人同意”行使集体意志。在组织形式为公司型基金的情形下,则应参照《公司法》股东会决议机制进行操作。
2、指定临时管理人,接管基金核心职能
当原管理人严重失职或拒不履责时,基金机构可尝试通过投资人会议决议指定“临时管理人”或临时执行事务合伙人,以保障基金资产不因管理真空而遭受重大损害。
目前,部分地方法院已在实务中认可投资人集体指定第三方临时接管机构(如律师事务所、清算专家)作为过渡安排,并给予资产调查、运营支持、资金监管等有限职责。这类机制虽缺乏明文立法支撑,但在实务中具备较强现实可行性,关键在于资料准备充分、权属清晰、操作规范。
3、依法行使股东派生诉讼与代表诉讼权
对于项目公司层面董监高失联或不履职的情形,若基金持有项目公司股权,可直接以“公司股东”身份提起派生诉讼,要求追究董监高因不作为或损害公司利益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如果管理人拒不代表基金发起诉讼,部分法院也开始探索在特殊情形下由出资人(LP)以“实际利益受损方”身份提起代表诉讼。例如,当GP存在严重违约、关联交易或因与被告存在利益冲突而拒绝诉讼时,LP可请求法院赋予其代理基金提起诉讼的权利。
该路径虽具争议性,但逐步获得部分地区法院的认可,尤其在管理人已实质性失控的情形下,成为机构维权的重要补充选项。
4、联动监管及司法机关,提升追责效能
如管理人或董监高行为涉嫌非法集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刑事犯罪,机构应及时通过正式渠道报案,并配合公安、检察等机关提供合同文本、财务资料、交易流水等初步证据材料。
在符合法定程序的前提下,也可结合民事附带刑事诉讼路径同步进行资产保全与责任追究。此类做法虽然对案件结果的掌控程度相对有限,但在面临基金资产遭受严重损害或彻底失控的局面下,往往是保护基金底层资产安全、控制舆情风险的必要手段。
三、“纸上维权”到“寸步难行”
虽然私募基金在管理人失控或董监高失联的情况下存在一定的法律救济路径,但在实务操作中,机构往往面临多重掣肘,导致权利主张进退两难,治理机制形同虚设。核心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基金合同条款缺乏应急治理机制
多数私募基金合同的设计更侧重于平稳运营阶段的权限划分与收益分配,而对极端情形下的“治理失灵”问题准备不足。例如:
·缺乏对管理人严重违约、失联等情形的具体应对条款;
·对投资人会议的召集条件、表决机制未作操作性强的安排;
·缺少替代管理人或临时接管机制的约定与授权路径。
上述缺陷导致基金一旦陷入管理人无法履职状态,即面临“无章可循”,投资人虽然意识到问题,但在程序路径上无法形成统一行动,维权进程停滞。
2、权利主体模糊,法律定位尚未厘清
目前法律体系中,尚无专门规定当基金管理人怠于履职或失联时,LP是否可直接行使代表基金诉权,司法实践中对此也存在较大分歧:有观点认为,基金为独立法律主体,诉权应统一由管理人代表行使,LP无权越权;另一类观点则认可在管理人实质失控的情况下,LP可“补位行权”,法院可在审查基础上作出例外允许。这类法律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机构维权的可预期性,也增加了法律成本与时间成本。
3、执行路径碎片化,缺乏统一协调机制
基金失控后的权利主张往往涉及多个层级和维度:对管理人发起违约追责、对项目公司进行资产控制、对实际控制人进行刑事举报等。但当前法律实践中,缺乏系统性的执行协同机制:民事、刑事与行政路径各自独立,信息共享效率低;地方监管机构协助能力存在差异,协调机制滞后;多方主体(LP、投顾、外部中介)职责不明,导致维权行动碎片化、低效化。上述问题叠加,使得私募机构即便愿意维权,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系统性、高效化的应对方案。
四、从失控到自救
面对管理人失控与董监高失联等极端风险事件,单纯依赖事后维权往往为时已晚。对于私募基金机构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度层面提前做好预案,同时在事后处置阶段建立有力的应对机制,实现“事前防范 + 事中控制 + 事后追责”的全周期治理闭环。具体建议如下:
1、强化基金合同与章程的治理预设机制
私募机构在基金设立初期,应对基金合同及组织章程条款进行前置性审视与优化,重点在于:
·明确“管理人失联”、“重大违约”、“不能履职”等应急情形的认定标准;
·设定LP可召集投资人会议并替代管理人决策的条件与程序;
·预设临时管理人选聘机制,并明确其权限边界及存续期间;
·授权投资人或其代表在特定情形下提起代表诉讼或采取资产保全措施。
2、落实投后管理制度,建立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
在基金运行过程中,应强化对管理人履职行为的持续性监测与风险识别,具体可包括:
·引入定期投后核查机制,对信息披露异常、操作频率突变等行为及时干预;
·将关键事务授权、资金划拨、重大决策等事项纳入“多重签字”或“双重审计”体系;
·组建专门风控团队或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底层项目治理进行穿透式监控;
·对管理人核心人员变更、项目公司治理僵局等突发事项,建立“响应预案”及职责清单。
3、多路径并行推动追责与资产控制
在事后处置阶段,机构不应单一依赖某一途径维权,而应构建“民事+刑事+行政”联动框架,形成复合式博弈策略:
·通过律师团队迅速厘清基金账户、项目公司资产结构与控制链条,申请查封、冻结及财产保全;
·若存在资金挪用、侵占等犯罪嫌疑,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推动启动刑事程序;
·积极与行业协会、基金业协会或地方金融局沟通,争取行政协助介入,提升维权效能;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联合其他LP或基金份额持有人组建“维权联合体”,提升话语权与执行力度。
基金管理人失控与董监高失联,暴露的不仅是个别主体的治理失职,更是私募基金制度设计与风控体系的系统性缺口。对于私募基金机构而言,唯有在制度预设中预留应急空间,在投后管理中强化风控闭环,在事后追责中运用多元路径,才能真正构建起抵御极端风险的防火墙。治理的沉默成本极高,而预防性的制度安排,将是机构稳健经营的压舱石。
文 | 夏叶璐
编辑 | 麻艺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