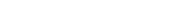近10年来超2.4万家私募管理人注销、年内超千家机构退出市场,私募基金行业的 “出清浪潮” 正从政策驱动的阶段性清理,转向监管与市场共同作用的常态化机制。其中,强制退出已不再是偶发个案,而是成为净化行业生态、加速优胜劣汰的主流选项,深刻重塑着资本市场的私募格局。
强制退出成主流:
数据背后的行业变革
私募基金强制退出的主流化趋势,有着明确的数据支撑。据中基协统计,截至2025年10月13日,近 10年间已有24171家私募管理人注销离场,其中 2022 年以来的新一轮出清尤为显著 ——2022年注销2210家,2023年峰值达2537家,2025年截至10月已有1014家退出。
从退出类型来看,强制属性的 “协会注销” 占比持续走高。2025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协会注销” 以 275家的数量占据同期注销总量的52.68%,成为最主要的退出方式,远超 “主动注销” 的45.97% 占比。这些强制注销案例中,既包括失联未整改、违规运作的问题机构,也涵盖长期无在管产品的 “僵尸机构”,彰显了监管层 “扶优限劣” 的坚定态度。
值得关注的是,强制退出的覆盖范围已从早期的 “空壳私募” 扩展至各类经营失范主体。2025年以来,已有超50家私募机构收到中基协罚单,部分机构因信息披露违规、出借 “通道”、违规交易等行为被撤销管理人登记,甚至遭遇监管 “双罚”,强制退出的惩戒力度持续升级。
在什么情况下能申请基金强制清算?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7条的相关规定,法院应予受理的强制清算申请的三种情形包括:
(1)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
(2)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
(3)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
在司法实践中,基金强制清算案件并不常见,而在法院受理的,为数不多的此类案件中,申请人大多均以前两种情形作为申请理由。例如,在上海超人电气有限公司与上海婺商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申请公司清算强制清算案【(2021)沪7101强清120号】中,案涉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因为基金出现了法定解散事由(即合伙期限届满)但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而在天津雷石合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天津雷石泰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纠纷强制清算申请案【(2021)津02清申133号】中,案涉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基金的部分有限合伙人拒绝配合其办理基金的工商注销手续,导致无法完成自行清算为由(即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
下面,我们拟结合一则案例就强制清算的第一种情形进行引申分析。在唐敏、深圳市大正元成长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申请公司清算强制清算案【(2019)粤0304清申27号】中,案涉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唐敏以从未获得过案涉基金的分红,无法知晓案涉基金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且案涉基金拒绝召开合伙人大会等为由,认为案涉基金已无法实现设立目的,向法院申请基金强制清算。而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出的“案涉基金已无法实现设立目的”的理由(“不分红、不开会、不给查账”)并非强制解散事由,而且案涉基金并不认可其已发生解散事由,故在解散事由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申请人申请对案涉基金强制清算缺乏依据,不予受理。法院同时指出,强制清算主要是一种程序制度,不具有解决实体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功能,双方对于是否发生解散事由的争议,应另案解决。
由此可见,强制清算的第一种情形“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核心在于对“公司解散”的认定,即:是否出现了《公司法》规定或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如果法院认定并未出现法定或约定的解散事由,那就“此路不通”了(即申请人无法以案涉基金解散后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申请强制清算)。因此,建议广大私募基金投资者,尽可能在拟投基金的基金合同/章程/合伙协议等文件中,具体约定基金解散的事由,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掌握退出基金的主动权。
三重推力:
强制退出常态化的核心逻辑
监管门槛实质性抬升
2023 年 5 月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及配套指引,将私募行业门槛提升至 “类公募” 水平。私募证券产品初始募集规模从 100 万元大幅提高至 1000 万元,且需全年维持平均资产规模达标,直接将大量募资能力薄弱的 “草台班子” 挡在门外。同时,存续期合规成本显著增加,人力、场地、审计等年度运营支出达百万级,让无力负担的中小机构难以存续,最终触发强制退出条件。
市场环境加速淘汰
资本市场波动加剧了私募行业的生存压力。股权类私募受 IPO 节奏放缓、项目退出难影响,超额分成无法实现,长期锁定期基金发行遇阻;证券类私募则陷入 “业绩下滑 — 规模萎缩 — 管理费锐减” 的负向循环,不少机构因规模跌破清盘线、无法覆盖运营成本而被强制清退。这种市场驱动的自然淘汰,与监管强制退出形成互补,共同加速了行业洗牌。
常态化监管机制落地
监管层已建立起系统化的强制退出核查机制。对于 12 个月无在管产品、公示期满未主动联系协会的失联机构,中基协实行定期批量注销,仅 2025 年就有多批失联机构被强制清退,其中单批注销数量达 15 家。同时,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持续加大,深圳证监局等地方监管部门多次曝光出借账户、市场操纵、非法配资等乱象,相关涉事机构均被纳入强制退出名单,形成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的监管常态。
行业新格局:
强制退出下的生存与发展
强制退出的主流化,推动私募行业从 “野蛮生长” 向 “高质量发展” 转型。一方面,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存续机构数量从峰值稳步回落至2025年8 月末的19614家,头部机构凭借品牌、业绩和募资优势实现 “强者恒强”,中小机构生存空间进一步收窄。另一方面,行业生态持续净化,“伪私募”“乱私募” 等增量风险得到遏制,约7000家僵尸机构完成出清,为合规机构腾出了更多市场空间。
对于留存机构而言,合规与专业成为核心竞争力。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私募行业的竞争将聚焦于三方面:可持续的优秀业绩、稳定的募资能力、规范的运作体系。国企背景、上市公司系私募凭借资源优势加速崛起,而个人系中小私募需通过差异化定位、专业化投研实现突围。
结语:
强制退出引领行业走向成熟
私募基金强制退出的主流化,并非行业的 “寒冬”,而是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然阶段。它通过监管与市场的双重筛选,剔除无效供给、防范金融风险,既保护了投资者利益,也为优质私募创造了更健康的发展环境。
随着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强制退出将持续作为私募行业的 “净化剂”,推动行业从 “量的扩张” 转向 “质的提升”。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一变革将加速形成 “合规者生存、优秀者发展” 的良性生态,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资料参考 | PE与TMT法律桥
编辑 | 麻艺璇